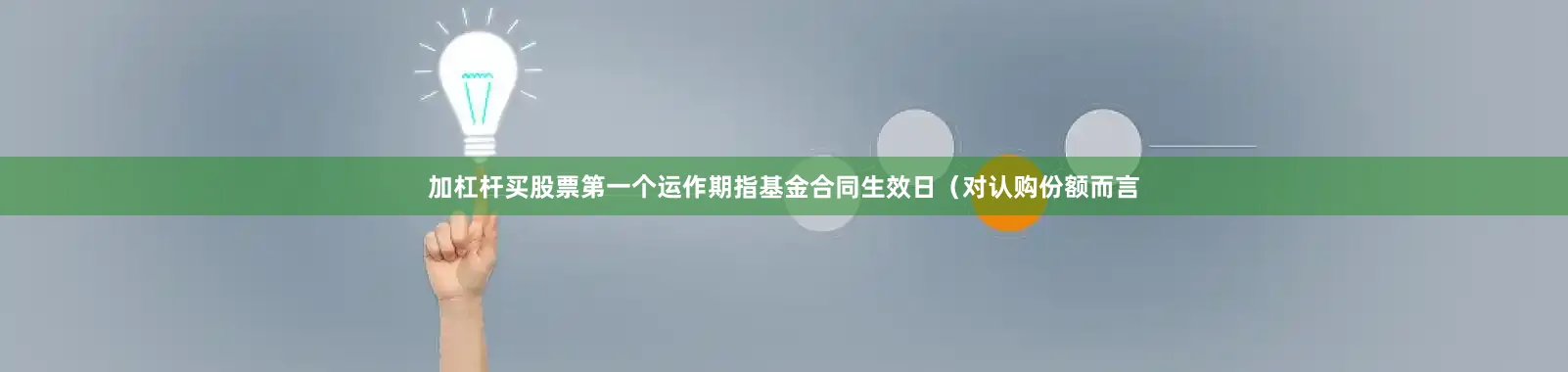2025年8月4日,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在美国去世,享年95岁。他毕生致力于中国历史、文化研究,以上古史、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及独树一帜的“大历史”写作闻名于世,其代表著作包括《中国古代社会史论》《汉代农业》《西周史》《万古江河》等。许倬云虽以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史为研究重心,但目光从未局限于中国古老的过去,而是由思考出发,观察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与发展。资深媒体人李菁在新书《历史的钟摆》中收录了她在2022年、2023年对许倬云先生的访谈。
《历史的钟摆》
李菁 著
火与风|上海译文出版社
经明行修是基本素养
李菁: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的大一统的共同体,发展了几千年,为什么现在面临那么多各种挑战,一直没有崩坏,也没有分解,背后核心的原因是什么?
展开剩余89%许倬云:中国历史上面临的外部挑战,一个是饥饿,另一个是侵略。农业是自生自长的事情,农业好的时候,凭两只手就能养活全家。以农为本的中国,在汉代以后已经平稳地发展出“精耕细作”的农业。因此,只要田亩足够,在安定的局面下,就可以做到以足够的劳动力,养活足够的人口。
作为农业国家的中国,如果有问题,一则天灾,一则人祸。前者不会永远发生,也不会全面而持久地发生。因此,中国的农业,只要没有重税、没有重租,且劳动人口不减少,那么这种农业秩序基本可以长期维持稳定。
“人祸”可以分成两种:一则是国内秩序失衡,政府的管理制度失效,于是农家无法有安定的日子维持正常的生产;另一则是外敌侵犯。
过去的外敌主要是北方和东北方向的游牧民族——他们居住在气候比较寒冷或干燥的草原地带,牧养经济生产力并不稳定,遭逢天灾——长期寒冷或干燥,会让他们向南侵犯,寻找更好的牧场。北族南犯中原,铁蹄进入阡陌纵横的农地,难以驰骋。而且中国可以不断地向侧面或南方撤退,维持长期的抵抗。北族通常无法熬过这样的“消耗战”,终于被中国消灭或同化。
这种外族侵犯的个例,可能长期不断地出现。因为邻近中国的外族先企图进入中原,更远方的邻居便一群群地跟随前面的“开路先锋”,尝试牧马中原。于是,这种灾害——例如“永嘉之乱”时期,可以持续三四百年之久。另一种形态是从契丹以至于蒙古,接下来是女真满族——这种长期一波一波地侵扰中国,胡汉之间不断地更换角色、互相进退。如此后果,就是汉人政权和胡人政权轮流占有中国,甚至建立“二元体制”:北族以北方当作自己的“老地盘”,以草原方式继续经营,也作为其维持中国的后援;而在汉地,则收取钱粮,维持汉地“中国式”的朝代。
所以,“中国”这一含义不断地变化:从现在的黄河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——长江流域的总生产力数倍于黄河流域;进而扩到沿海地区——虽然那片区域较小,可是进一步扩大到西南,力量就大了。上述制度,以满清政权维持最长期而稳定的“二元体制”。因此,“中国”的内涵也就在其制度之下,潜移默化地转变成现代国家(而非完全汉人)的基础。可是,清代始终只能做到“前现代”的体制,这种牵绊永远不能将其转变成现代式的国家体制。
如前所述,还有一种形态的朝代更换是由于农民起义。农民平常安居乐业,假如政治环境良好,即使有天灾或者疾疫,只要政府功能正常,通常可以赈灾或移民的方式解决这一困难,而不至于颠覆政权,更不会颠覆“精耕细作”的农业经济。
李菁:怎样理解中国的文官制度?
许倬云:中国从汉朝起就讲“经明行修”:通晓经学、品行端正的人,就是“士”。但是他们要想进入太学,就需要经过一定的选拔程序。他们会选一部经典作为自己修读的专业,要保证学术思考能力过关——就像我们写论文一样。太学毕业后,这些人回到家乡:大概有十分之一的人可能会被推荐到地方政府,从基层开始,逐步升迁,最终进入中央政府。
如此情形之下,这些知识分子除了必须具备“经明行修”的基本素养,还要有“牧民之责”。按照《论语》的意见,候补官员如果能够做到修己,再进一步做到安民——也就是说,如果他们有德行和能力,就足以治理国家。《论语》的盼望不仅仅是“安民”,还有“安百姓”——此处“百姓”的意思是“百族”,也就是许多其他族群。到了那一阶段,就是从一般的国家终于开展为“天下国家”。只是,儒家也觉得这一理想实在遥远,所以不一定能做到,甚至不必马上做到安顿整个“天下”。
“精耕细作”只是自家土地的充分利用
李菁: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资本主义,这一直是学界争论的话题,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做了分析。您的观点是什么?几年前,学者彭慕兰在《大分流》一书中提出“欧洲例外论”,您怎么看待他的研究?
许倬云:儒家“治天下”或者“安百姓”,是个遥远的理想。中国儒家真正的理想不是想做霸主,最多管到四邻,互相不侵不犯。明太祖立国之后就宣告,四邻有十四个“不征之国”,也就等于宣称“你不犯我,我不管你”,彼此睦邻共存。明成祖派遣舰队“下西洋”,先后六次大舰队航行,没有灭掉任何一个国家。
西洋的历史则是摆明了由贸易取得最大程度的利润:经济获利为第一步,下一步即是“通盘接收”,乃是贸易转为殖民,以完成全盘的掠夺。从16、17世纪开始,西洋人经过远航,纷纷割占世界各地,那是一个全盘征服的制度,而用“天下国家”的口号作为借口。这种“天下国家”,以力量为本钱,而不是以治理、安顿为目的。资本主义的趋利,是“极限的获利”。中国“精耕细作”基础的农业经济,只是家门口自家土地的充分利用。二者之间的差别就在于中国制度是大家共有“天下”;资本主义的制度,则是“唯我独尊”——做不到统一的时候,至少要做到一方之霸。中国式的天下是农业的,不会想到全球都是农田;欧美式资本主义的“天下”则是赚钱唯恐不多,财富没有止境,那才是真正走到极限才停止的制度。
明代几乎可以和欧洲的商业化社会个别而平行地发展。只是为何明代没有走向欧洲同样的历史途径?
我的观点是,第一大原因是生产力:机器生产当然比手工生产快,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——对明朝而言,为什么要大量生产?生产出来的东西卖到哪里去?为什么欧洲需要市场,中国不需要市场?因为中国可以自给自足——村子里卖不动就到镇里卖,镇里卖不动就到县里卖,这就足够了。
但是西方从西班牙开始,到英国、美国,是要将生产的商货转卖他人以赚取财富。所以,欧洲人发展出来的模式是:商业资本主义+工业机械化生产。工业机械化来自两方面:一个是矿场里拉煤的机器,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;另一个是船上加一个机轮,跑得快、跑得远——这两样东西都是为了生产出廉价的产品,卖到他方赚大笔的钱。可以说,这是“另一种方式的游牧”,他们的掠夺不靠传统的鸣镝、快马,而是凭借机械和商品。
李菁:古代历史上的东西方贸易,中国的大宗商品卖出去依然会产生巨大的利润,白银持续流入。既然有这样的外销渠道和大市场,为什么没有把这个轮子转起来,更没有转得更快呢?
许倬云:从宋代开始,官方介入榷、监等类生产事业。榷、监中的工作人员中,相当大一部分是皇室成员或来自功勋家族,他们不隶属于一般的政府官僚组织,而是以皇家专营的方式维持特权。好处是:既然他们是特殊人员,日久以后,多少有点专业训练;他们手下的技工,也因为职业相当有保障,愿意专心致志地改良产品。我以为如上这些条件,使得宋代的手工业和专业生产能够提供大量的产品——不仅内销,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外销至东亚乃至印度洋。因此,宋代这种产业的数量,在全世界的生产当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。
上述“官办企业”,例如烧瓷、冶金等,生产量大,利润也厚;所得利润则用于供应皇家与贵族生活,并没有将资本投入再生产或企业的升级。自宋以后,这种体制在中国维持不断;到明代,是太监代表皇权监督产业;在清代,是内务府独占产业。数百年来的专断,这种体制惰性逐渐显现,而且成为痼疾,以至于不再可能转化为健全的市场体制下出现的资本主义。
动态的“善”与“和谐”
李菁:您的著作里面常有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源流的对比追溯,怎么样去理解中西方两种不同的哲学观点?
许倬云:希腊的大哲柏拉图,在其老师苏格拉底离世前与他讨论了这个问题:他们求真——“真”“善”应当一体,而他们也是如此认为的。但是,希腊神话中的生活不是“善”,而是相当的任性。众神都行为不端、男女情爱混乱不堪,柏拉图认为因为神话中的混乱,在一个已经进入文明的城邦,就该思考如何从求“真”进一步求“善”。苏格拉底认为,他自己所见的城邦制度并不理性。因此,所有城邦呈现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现实,都有极大的缺陷。城邦之中,既然所见的只是原始欲望的将就,那么,如何以“善”为方向,在混乱之中找出合理的秩序并预防目前的城邦制度会走向“不善”的成分,如僭主、暴民等,就成为他们需要思考、面对的问题。
他们看见城邦内部出现暴力的苗头,所以要针砭城邦,要浓缩道德之学,所以主张“哲人王”管理国家。这一“哲人王”不是直接做王,而是监督城邦——以良心来监督。
从这一出发点来看,西方传统有两个东西:一个是游牧、战斗部落的权斗,也就是为了酒色财气、欲望、淫乱、权力;但是,在这时候永远有一个头脑清醒的人,替老百姓看天象、气候(有时候还看地理形势),类似中国古代“姜太公”的角色,他们后来有的成为“博士”,有的成为“先知”。
这一转换在欧洲非常不容易,但是在中国相对容易:中国的大部分地方是农耕——农耕是生命的再造,没有善恶可言,只有因时而动。因此,在中国“天人合一”是农业生产的和谐得来的;游牧民族的“善恶对立”,实际上是“顺我者昌,逆我者亡”的强暴。
李菁:您在书中也说到类似观点,说中国思想的二元观,甚至多元并存的观念,都会综合成辩证的推演,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文化缺乏绝对理性的追求呢?
许倬云:传统的中国思想不追求绝对理性,而是追求最终的“善”与“和谐”——二者都是动态的。比如:教育一个所谓的“坏小孩”,你用软的办法感化他,可能比较合适;若是用坏的办法惩罚他,这个孩子可能就被毁了。对于自己,同样如此:可以用善的办法自我反省,发现“我错”,则自我纠正,不用自以为是,斗人为乐。
李菁:这种动态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,但是为什么到了南宋以后,朱夫子解释的儒家伦理又变成一个固定僵化的结构呢?
许倬云:朱夫子的思想是“结构论”:有一个四平八稳的秩序,这是一个已经设定的“理想结构”。于是,君臣之间就如天地之间:明君英主代表了最善的秩序。但是,下一步的推演,只要是“君”就是“明”,只要是“主”就是“英”——有了这种预设,君臣之分就不容僭越,上下之间就是自然的秩序,不容挑战,更不容颠覆。
(本文摘选自《历史的钟摆》,内容有删节,标题、小标题为编者所加)
发布于:山东省股票怎么开户,配资指数网官网,南京股票配资平台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